 感謝工作人員的安排。
雖然仍是不夠積極與異性互動熱絡,但希望能早日找到幸福。
...
(詳全文)
感謝工作人員的安排。
雖然仍是不夠積極與異性互動熱絡,但希望能早日找到幸福。
...
(詳全文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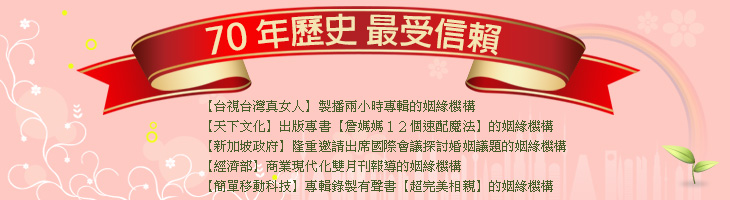
|
Friday, July 15, 2005, Vol. 1 |
|
作者:張蘊之 |
|
莎士比亞不打卡 |
|
|
|
初夏,我還不習慣晨起。三十層高的辦公大樓外是綠但不刺眼也不雄偉的象山,雖然不是第一次扮演上班族的角色,卻是第一回這麼貼近商業,這麼頻繁地聽見高跟鞋卡卡卡的聲音,和這麼多人一樣,在早晨的捷運上睡著,睜著惺忪的雙眼急急忙忙步出捷運站,與打卡機的數字賽跑。 對於這個新身分,我是相當抗拒的。從來我就不覺得自己是個會在辦公室一坐就坐上九個小時的人,雙眼除了盯著電腦螢幕,什麼事都不能做。雖然學生時代也是這樣長時間在電腦前面工作,但畢竟是做自己選擇的事情,而不是被交代、與主觀意識無關的工作。這份職業來得快又急,我還來不及適應這個世界,還來不及調整時差,來不及習慣二十四小時中,有超過十個小時的時間是為薪水而活的日子。 陽光對我而言是種煎熬。上班第一天,我大大咧咧地在辦公室裡捲我的煙,推開小小的落地門,在僅容一人轉圜的小陽台透氣。這種行為立刻引起一陣騷動。同學在msn上傳來訊息,不勝唏噓地說:「妳就這樣突然消失了,我們超不習慣的啊!」 過去那個總是背著書包在系館裡逛來逛去,大談對藝術的執著與憧憬的身影,突然就這麼消失了。當我在捷運上總是睡著,醒來向公司方向發足狂奔的同時,在對著面前的電腦長吁短嘆的同時,過去的自我認知與價值感都被所謂的「社會機制」給瓦解了。坐在辦公室裡的那個女孩,只是一枚功能鍵,被輸入指令後執行工作程序的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。 公司要求我繳上一個英文名字,我把在網路世界中用慣了的代號呈了上去,結果又引起一陣騷動。過了一段時間,所有高層都強烈要求我改名字,我只好把中文名字翻成英文,改了一次又一次,才算勉強通過。點點滴滴,都在消解我過去堆累許久的身分,那個做劇場的我,那個總是在接雜誌特約採訪的我,那個曾經在某藝文專業站保有一塊筆耕園地的我……,一旦走進辦公大樓,就一切都失去意義。 女同事們都化著妝來上班,帶著小小的包包,踩著高跟鞋。我換上高跟鞋,卻發現每天這樣走來走去,鞋底很快就磨損了,透出的鐵釘敲在大理石的地面上,十分刺耳。我換上小包包,小包包裡放了一隻摺傘、一個錢包、一個化妝包、一本名片簿,就已經滿得快爆炸了,提在手上沒多久,由於過重,車線的地方出現了裂痕。 每天在公司唯一的消遣,就是打開零食櫃尋找犒賞自己的各種可能。於是體重直線上升,兩個禮拜的職場生活,就已經胖了五公斤。而且鎖在椅子上,完全不合乎人體工學的鍵盤讓肩膀長時間保持高聳,肚皮長時間保持鬆弛,屁股長時間保持癱軟,我深深感覺自己的骨骼與肌肉高舉著抗議牌怒吼。沐浴在冷氣房的過敏鼻則不停發炎腫脹,倒流的鼻涕時不時就引起喉嚨跟著疼痛起來,黑眼圈日益嚴重,鼻塞則讓黏膜乾枯泛血雙眼發酸,腦袋也隨之昏沈。 「辦公室絕對是不健康的。」回家我跟媽媽抱怨。以往在劇場生活,每天蹦蹦跳跳,吃得少運動量大,雖然年過二十五,看起來還是像個大學生,那種燃燒青春的光采、對自我的高度要求,也是長保活力的重要原因。媽媽卻反問:「上班就是這樣,妳不上班還能做什麼?」言下之意,就說明了「職場是人活著必經的過程」。 但我是不服氣的。此時才真真正正體會到劇場前輩對自己「從來沒上過一天班」的那種驕傲來自何處。上班真的會把一個人搞到懶得想望未來,每天回到家就只能看沒營養的電視,攤在沙發上把遙控器按到爛為止。 不服氣又能怎麼樣呢?我想起舞蹈界的P。還沒認識他之前,他就是一個傳奇。據說他白天在做建築師,晚上就排舞練舞,而他的同事完全不知道跟自己處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的P,是舞蹈界的重量級巨星。 十幾年來,P就是這樣過著他雙重身分的日子。其實不上班是真的餓不死人的,到處接一些有的沒的case照樣過日子,只是沒有安全感而已(但會很有成就感)。沒有一個「職稱」就是失敗者嗎?我對這樣的社會眼光,感到心寒。躲在小陽台抽煙的時候,我常常想起哈姆雷特那段台詞:「世界是一座監獄,而丹麥,則是其中最糟的一間。」 The world is a prison,be an office lady,is the worst one。 閱讀次數:3121
|
張蘊之,LJ專欄作者。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,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進修中,為《表演藝術雜誌》、《誠品好讀》、《幼獅文藝》特約記者,平日在信義計畫區某公司擔任文案企劃。還沒變成上班族之前,在劇場裡逛了七年多,生活中除了讀書做戲看電影、喝酒抽菸看醫生、接接稿子打打工,沒有其他太正當的活動。曾獲西子灣文學獎,至於為什麼沒有別的得獎紀錄?她說:「為文學獎寫文章太不自在。」
上一則 回總覽 下一則